
包來秋和妻子站在被燒毀的老屋里,說起10年來的流離失所顯得有些傷感。
經歷了種種天災人禍,溫嶺市石塘鎮鹽南村村民包來秋如今說起自己的遭遇,無奈中仍帶著點希望。
從遭遇火災到生意虧本,包來秋一直在磨難里顛簸,妻子說他不愛說話,也不懂抱怨,但如今這事,他們不得不抗爭。因為他們明明持有合法有效的國有土地使用證,卻蓋不了房,而這10年來,他們的土地上一直蓋著別人的五層小樓。
現在,包來秋求助本報,希望能把這個“啞巴虧”吐出來,得到他應有的土地。
一場火災使一家人成了住房困難戶
1998年的一場大火把包來秋一家人的老屋燒了個精光。
1998年以前,這個占地58.64平方米磚木結構的兩層老屋里,住著一家4口,包來秋夫妻倆、老母親和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女兒。
火災以后,鹽南村村委會將村部辦公樓騰出一間來,讓包來秋一家搬去暫住,包來秋的母親則在老屋的遺址邊上搭了間矮小的棚屋勉強居住。
隨著一年后老村部拆遷,包來秋一家三口不得已搬了出來,和老母親擠住在只有十余平方米的棚屋里。
9月12日中午,在這間臨時棚屋里,記者看到,它被分隔成前后兩間,一間臥室只有七八平方米,包來秋告訴記者,那些年,他和妻子女兒擠在臥室的床上,老母親只能睡在狹小廚房的躺椅上。
這樣的狀況直到5年后才開始緩解,經過鹽南村默許,2004年包來秋在自家的自留地上蓋了一幢簡陋的臨時住房,三人從母親的棚屋里搬了出來,2006年又添了一個小兒子,一家四口在臨時住房里一直住到現在。
包來秋家的住房困難在村里幾乎盡人皆知,所以在后來,被列為住房重點安排對象。
一次生意失敗令他空有土地無錢蓋房
2003年,鹽南村爭取到了一批建房指標,經過村兩委及村民代表同意,包來秋順利取得了住房指標。
據了解,當年鹽南村共31戶村民取得了建房資格,這批房子如今是一幢幢連體高樓,矗立在靠近大路的村北邊。
村民們的建房申請報送溫嶺市建設規劃局后,包來秋領到了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開始打地基。
也是這一年,為了多掙點錢,包來秋跟隨小舅子外出種西瓜,不幸的是,一場臺風令西瓜地嚴重受災,他血本無歸還欠了不少債,如今只能靠跑運輸掙錢養家。
生意虧本后,包來秋回了村,找到當時的村民主任金濟順。
金濟順回憶當年的情況說:“包來秋來找我,說種西瓜虧了本,房子不能起了。我跟他說,如果不想將土地轉讓的話,就先還給村里,等下一次有土地指標了,我們一定給他安排。包來秋主動將土地指標歸還了。”
10年來被人占地蓋樓
包來秋“歸還”土地指標后,鹽南村決定將指標轉給同村村民杜軍復。
金濟順告訴記者,同村村民之間進行土地調劑原本是件很平常的事,“說白了就是,你不用的土地,先給別人用,等你需要了,村里再給你調劑一間。”
但事實并不像大家想的這么簡單。包來秋“歸還”土地指標的時候,所有的土地審批手續都已辦妥,且這塊土地的所有權人已經確認為包來秋。
而此時,原本屬于包來秋一家的土地上,杜軍復的房子已經建好了,與其他9間民房,連成一幢整體的5層樓。
2008年,鹽南村有了第二批住房指標,包來秋再次提出住房申請。繼任村民主任在處理此事時被溫嶺市建設規劃局告知,土地使用者的名字改不了了。
直到2011年現任村民主任江志法上任,包來秋的住房難題就傳給了他。
江志法說:“我們和石塘鎮分管的副鎮長及土管部門領導進行過協調,最后決定采用調劑土地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農村,調劑土地有前提:一是未發生過土地買賣關系;二是需要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這兩條包來秋都通過了。”
然而,等所有手續都辦下來,到土管所的時候,經辦人發現這塊土地的性質已由集體轉為國有劃撥,不能進行調劑,對國有土地進行“調劑”意味著逃漏國家稅收。
調劑的路走不通了,村里提議采取經濟補償的辦法。“現在村里有商品房了,杜軍復家雖然建了房,但用的是包來秋的名義,所以仍然享有住房指標。我們當初建議他報名申請商品房,用商品房買賣中產生的利潤對包來秋進行補償,但杜軍復不同意。”
包來秋夫婦對此表示,“經濟補償我們不要,我們只想要一塊屬于自己的地,在村里有地方可以堂堂正正地住。”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造成包來秋一家如此窘境的原因十分復雜,其中10年前土地性質的突然轉變,農村整體住房審批制度導致村集體沒有及時進行土地重新審批等等都與此相關。
對此,記者將進行后續報道,并及時追蹤包來秋一家的“追房夢”。
 臺州頻道
臺州頻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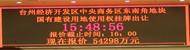 上海剛泰置業54138萬元競得臺州經濟開發區一地塊
上海剛泰置業54138萬元競得臺州經濟開發區一地塊

 路橋老太婆自創“名小吃”,很多人吃了幾十年也不膩!
路橋老太婆自創“名小吃”,很多人吃了幾十年也不膩! 各朝代的銅鏡是什么樣的?越地古銅鏡精品展帶你領略
各朝代的銅鏡是什么樣的?越地古銅鏡精品展帶你領略